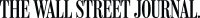記得頭一次聽到台灣是在國小六年級的歷史課上,當時我十二歲,國家歷經巨大轉變,從共產變成民主不到三年。而一直以來都讓我們生活在陰影之下的共產老大哥蘇聯解體,也不過才一年前的事。
當時我居住在一個不尋常的國家。前一天,商店空無一物(因為是公營商店);接著某天,政府允許民營,貨架上的商品便從最底層堆到最上層,而且都是作為孩子的我從沒見過或很少見到的東西:巧克力、香蕉、柳橙(共產時期,一年只有一次,也就是過耶誕節的時候,才能見到這些東西)。當時我的父母嚐到了即溶咖啡與西方啤酒的滋味,我們似乎頓時躋身為世上最好的一部分。
不過我們很快便知道這些繽紛美麗的事物皆有其代價。身為老師的母親丟了工作,因為轉眼間,我們已不再需要那麼多學校。這讓她患了好幾年的憂鬱症。好在她只是得了憂鬱症,因為在那個轉型的年代,說到自殺率,我們可是歐洲翹楚。
我就是在那段苦甜摻半的奇妙歲月裡從歷史老師那兒得知,當我們在波蘭飽受共產之苦的同一時間,台灣人多虧驍勇的蔣介石將軍,未曾嚐過那滋味。我當時覺得台灣歷史與波蘭歷史的走向類似,只是過得生活完全相反。在那個國家的歷史裡,多虧有蔣介石,不管是柳橙、巧克力、即溶咖啡還是西方的啤酒,台灣的國民全都能享有。
當時在我的記憶裡,台灣是個理想的國家,那個國家的人民不需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事。
五年前,我收到一封完全意料不到的電子郵件。
寄信人是傑出的波蘭文譯者林蔚昀小姐,告知台灣的衛城出版社想出版我的《跳舞的熊》。這本書講述的是我們脫離共產主義所經歷的艱辛與曲折:成年後,我見到越來越多我們在黃金的九零年代所經歷過的困難。當時丟了工作、還得對抗憂症的人不只我母親,像她這樣的例子書裡多有著墨。
收到信的當下我很開心,怕是作夢,回信前還捏了自己兩次。一本波蘭人寫的書,寫的是不懂適應自由生活,不斷重複奴隸行為的保加利亞的熊(其實我們人類也一樣),竟會有來自世界另一端完美國度的出版社想簽下版權,令人難以置信。我跟林小姐提出我的疑問。「您錯了。」她說:「這本書講的也是台灣,那裡的每個人都能了解這本書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理解這番話。
《跳舞的熊》兩年前在台灣出版,於此之前已在二十個國家發行,讀者會透過臉書和IG找到我,或者不知從何處挖出我的電子信箱,但我在全世界還沒收過像來自台灣這麼多的讀者來信。這讓我很訝異。不過若是一本書能在世界另一端的人心中喚起這麼多感受,這對作者來說是很大的滿足。這些人的成長背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卻能與作者共鳴,這會讓作者覺得自己寫了一個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