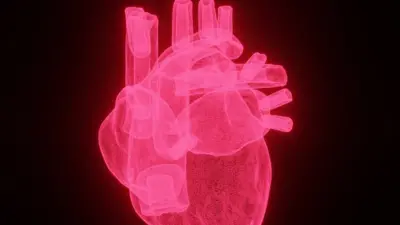救援任務:有如好萊塢電影的「南極救援行動」

圖像來源,Tim Nutbeam
- Author, 桑德琳·塞爾斯特蒙
- Role, (Sandrine Ceurstemont)
2015年4月下旬,努特皮姆(Tim Nutbeam)帶著一大袋血漿,登上了前往南極的救援飛機。此時正值南半球初冬,整個南極大陸被黑暗和嚴寒籠罩,強風頻頻來襲。由於氣候條件惡劣,在為期半年的冬季裏,一般不會安排任何航班在南極起降。
即便如此,英國急診醫學顧問努特皮姆還是同飛行員和工程師一起,飛赴南極。
他們是為了救助基地裏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幾天前,在哈雷研究站(Halley Research Station)工作的英國南極調查局工程師羅伯茨(Malcolm Roberts)腸胃嚴重出血,而最近的醫院卻在數千英里以外。
羅伯茨失血很多,但所幸挺過了前24小時。如果救援隊伍能夠及時趕到,那麼他還有一線生機——但是前往南極的路道阻且長,很難說羅伯茨能不能逃過一劫。
飛往哈雷研究站大約需要24小時,中途經停南極半島的羅瑟拉基地(Rothera)加油。再加上回程,總共需要連續飛行48小時之久。返程途中還要應對患者的緊急狀況,幾乎沒有時間休息睡覺。
單是拯救患者生命就已經不簡單了,而與此同時,努特皮姆能否做好這次任務的心理凖備?
最初並不是要派努特皮姆去,他只是後備醫生,緊急救助開始後他飛到了智利最南端的蓬塔阿雷納斯鎮,按照計劃是等救援飛機在那裏著陸後提供協助。

圖像來源,Tim Nutbeam
但是,小鎮以北的火山爆發,一切計劃都被打亂。主治醫生當時正在聖地亞哥等候轉機,但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智利南部與南極洲之間的德雷克海峽卻出現了難得的好天氣,海上能見度很理想。努特皮姆說:「我突然意識到該我去了,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事發突然,他承認當時甚至無暇思考可能發生的危險,只記得對前往南極救援激動無比。
極限探險者的品質
在南極冬天進行的醫療撤離屈指可數。2016年曾在24小時不見太陽的極夜裏用飛機接走過一名病人,另一次是2010年從美國的研究主基地接走的。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心理學研究員史密斯(Nathan Smith)表示,參加極限探險的人通常是想要嘗試大多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說:「這些人往往訓練有素,因而將這當成是一次檢驗技能並嘗試新任務的機會。」
面對極限探險的壓力時,某些性格類型的人會更加自如。有研究顯示,神經沒那麼敏感的人表現得更好。史密斯說:「我們發現,從事高危工作的人更不容易焦慮,即使焦慮也能控制好。」
這也與負責心有關。例如,一項研究調查了願意嘗試飛機拋物線飛行的人有哪些性格特質,結果發現責任心能讓他們更好地應對極端的要求。人們普遍認為敢於嘗試極限活動的人玩的就是心跳,但這項研究的結論恰好相反。史密斯說:「我們發現,這些人常常會花很多時間來降低風險,會盡力避免腎上腺素飆升,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危險信號。」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此次漫長的旅程中,努特皮姆和團隊必須積極應對各種困難。譬如,努特皮姆需要全程監控血袋的溫度,確保它處於有限的最佳溫度範圍之內。大家都擠在較為溫暖的機頭,機尾的溫度則低至零下10攝氏度。他說:「我得找個合適的地方放置血袋,而且每小時都要檢查一次。」
破曉時分,援救團隊成功抵達哈雷基地,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將羅伯茨運上飛機,再晚天就黑得無法起飛了。氣溫已經到了零下30攝氏度,寒風將體感溫度降得更低。努特皮姆坐著雪地摩托抵達基地,並在羅伯茨身上成功進行了南極第一例輸血,隨後把他轉移到了飛機上。與此同時,飛行員保持發動機運轉,因為引擎一旦過冷就再也發動不起來了。
努特皮姆表示,由於情況難以預料,他們的計劃也很粗略。他的策略是「隨機應變,恰當處理」。
史密斯和同事們在採訪過探險隊員後發現,自信要比太詳盡的計劃重要得多。他說:「然後就是要靈活處理隨機應變,要根據事態發展相機行事。有許多事情是你無法控制的,能接受這一點也很重要。」
睡眠嚴重不足
訓練有素、盡職盡責、滿懷信心,即使具備了這三點,也無法忽略可能是救援任務中最大的挑戰:飛行48小時所造成的睡眠嚴重不足。努特皮姆說任務中他一共就睡了四個小時,還說「他已經不是自己了」。
閉目養神不到半分鐘的微睡眠有助於恢復體力。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睡眠與表現研究中心的主任凡·東恩(Hans Van Dongen)說:「不能好好睡覺的時候,大腦會通過短暫休息來補充睡眠。」
但是微睡眠也會分散注意力,影響各種表現——一個人如果剛好在開車就很可能發生車禍。
在返回智利的長途飛行中,努特皮姆異常疲憊,甚至都忘了醫學知識,也無法下醫療決斷。這很危險,因為羅伯茨的情況需要時時監控,需要重要的醫療決定。例如在羅瑟拉基地附近時,飛機需要高海拔飛行以越過高大的山體,但是羅伯茨由於失血體內的血液循環量很低,要考慮如果不輸血,他的血量能夠承受多長時間的高海拔飛行。
「我需要根據羅伯茨的狀況做出決斷,但我沒法下定決心,我通常都很講求實效,從來都很果決。」努特皮姆說,他從未有過這樣的情況。

圖像來源,Tim Nutbeam
睡眠也能調節情緒,影響心情:如果睡眠不足,大腦裏情緒中心的聯繫就不那麼緊密,自我情緒控制能力就會下降。凡·東恩說,睡眠不足的人可能會特別暴躁,或是昏昏沉沉。
在航程後段,羅伯茨中風了,這也給努特皮姆增加了挑戰。為了穩定病人的身體狀況,努特皮姆要給他加大輸血,也增加了輸液和用藥。他回憶說:「當時我情緒上有些承受不住了。羅伯茨一定很難受,但他很堅強。」
史密斯說,知道缺乏睡眠的後果就能更好地應對。他說:「可以對此有所凖備,想想這些後果會如何影響自己做決定。」努特皮姆說他疲憊時很沒有耐心,如果知道這一點可能會有所幫助。
團隊合作
所幸有一個專門的團隊幫助努特皮姆控制睡眠不足時的情緒。除了同行的團隊外,還有一個遠程支援網絡密切關注他們的情況。
中轉停留期間能夠進行通訊,遠程團隊會向飛機救援小組通報天氣情況,幫助他們進行後勤安排。
努特皮姆還會定期向英國的上司匯報治療情況,以及在不同境況下要如何應對。
飛機在羅瑟拉基地降落時,羅伯茨再次腸胃出血。基地有位醫生可以幫忙,雖然努特皮姆已經精疲力竭,但還是寸步不離羅伯茨。
努特皮姆的上司從英國打來電話,將一切布置得井井有條。她讓努特皮姆交給基地醫生暫時接管,自己休息一下,畢竟在接下來的航程中,能照看羅伯茨的就只有他一個人了。努特皮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建議了。不然我會一直陪著他,最後一段航程身心都會更加疲憊。」
周圍有其他人時緊張情況會比較容易處理。史密斯說:「人在危險中如果能得到有能力人的支持,可以有效緩解壓力。」
這與團隊的狀態密切相關:如果一個團隊無法和諧相處,那麼整個團隊的運作勢必受到負面影響。不難從性格品質(尤其是令人愉快的品質)的角度推斷誰能成為一位好隊員。史密斯表示:「一般來說,在高風險下從事小組合作的人處理起人際關係更勝一籌。他們知道如何有效溝通,如何保持團隊運作。」
後續影響
離開羅瑟拉基地後,飛機最終在智利蓬塔阿雷納斯鎮著陸,羅伯茨被轉移到醫院並成功接受了治療,但努特皮姆卻覺得任務尚未完成。他說:「我真的不想離開羅伯茨,我想和他一起去醫院,雖然我當時已經連話都說不完整了。」
探險隊員回來後常有類似的反應。史密斯解釋說,他們在高強度的環境中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會對還留在那裏的同僚產生同理心。他們也很難將這種情緒向沒有類似經歷的人傾訴,因此有相似經歷的人會走得更近。
努特皮姆可以定期去醫院看望羅伯茨,每天都有例會討論康復情況,他也慢慢把狀態調整了回來。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史密斯說,任務結束後,人們會去思考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可能發生的事,這往往會持續三周時間。要是曾在任務中擔當重任,之後可能會覺得喪失了奮鬥目標,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能夠幫助心理過度。
史密斯說:「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寫工作報告,或者把自身經歷寫成故事都很有幫助。」
新的訓練方式也有所裨益。像宇航員、軍人這樣需要在極端環境中工作的人,凖備任務時一般要進行大量的模擬訓練,但史密斯表示很少有心理上的訓練。他說:「這好像少了一環。指導人們適應極端工作環境有很多可以做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救援只是急診室日常工作的一個極端案例罷了。
努特皮姆建議,趁還能充分休息的時候先在心裏演練救援。他說:「這樣能為睡眠不足做好心理凖備。」
事後再去回顧時,努特皮姆認為自己當時並不覺得會去參加救援任務,對自己的定位只是個備選醫生,因此沒有預先考慮那麼多問題。現在他意識到,任務過程中飛機很有可能不能起飛,他們也可能受傷。他說:「回憶一次成功的救援固然讓人開心。但也要去想一想有哪些地方可能會出現問題,能不能避免。我到現在還會去想這些問題。」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