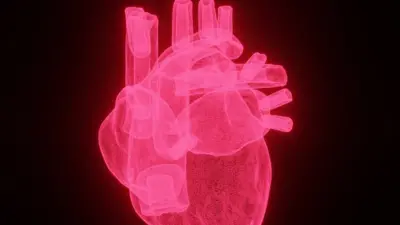圖輯:「如果企鵝會飛」野生動物攝影作品

圖像來源,Frank Deschandol
- Author, 埃利·戈登
- Role, (Elie Gordon)
《死亡的攀登》,攝影者:弗蘭克·德尚多爾(Frank Deschandol)
在秘魯亞馬遜雨林的一次夜間野外考察中,弗蘭克·德尚多爾發現了這種長相怪異的象鼻蟲,它依附在蕨類植物的莖幹上。
它呆滯的雙眼表明它已經死了,胸部長出的三根天線狀的「觸角」是「殭屍真菌」成熟的子實體。寄生真菌在象鼻蟲活著的時候就在它體內傳播,控制了它的肌肉,迫使它往上爬。當真菌生長到合適的高度時,象鼻蟲就會牢牢地抓住莖。在象鼻蟲內臟的刺激下,真菌開始長出頂部是膠囊狀的子實體,它們釋放出大量的微小孢子來感染新的獵物。德尚多爾透過虛化的方法突出了膠囊狀的子實體。第二天,當孢子被釋放出來時,真菌也枯萎了,這個致命的任務完成了。

圖像來源,Peter Haygarth
《獵豹和非洲野犬之戰》,攝影者:彼得·海加斯(Peter Haygarth)
在一次罕見的遭遇戰中,一隻孤獨的雄性獵豹被一群非洲野犬襲擊。由於棲息地的被破壞,這兩個物種已經從它們以前的分佈區域消失了,每種都只剩下不到7000隻。
在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KwaZulu-Natal)的Zimanga私人禁獵區,彼得·海加思開車跟著這些非洲野犬。一隻疣豬剛從非洲野犬群中逃出來,領頭的幾只非洲野犬就碰上了那只獵豹。起初,這些非洲野犬很警惕,但當剩下的12隻非洲野犬到達時,它們的信心增加了,開始包圍住這只獵豹,興奮得嘰喳直叫。年長的獵豹發出嘶嘶聲並向非洲野犬衝過去,它的左耳已經咬得破破爛爛,右耳朵則在喧鬧聲中。在晨光中飛揚的塵土中,海加斯把注意力集中在獵豹的臉上。幾分鐘後,獵豹逃走了,這場戰役也結束了。

圖像來源,Diana Rebman
《冷飲》,攝影者:戴安娜·雷布曼(Diana Rebman)
在日本北海道一個寒冷刺骨的早晨,戴安娜·雷布曼看到了一幅令人愉快的場景。一群長尾山雀和沼澤山雀圍著一根掛在樹枝上的長冰柱,輪流啃食冰尖。在這裏,一隻長尾山雀要盤旋幾秒鐘,才能喝到它的「冷飲」。如果太陽出來了,冰柱滴下一滴水,下一隻「排隊」的山雀就會啜飲而不是咬冰柱。這場「喝冷飲」的活動進行得是如此之快,就像精心編排過一樣。
兩天後,雷布曼回來了,發現氣溫仍在-20°C(-4°F),冰柱還在,山雀們還在喝著冰柱上的水。但當太陽出來後,冰層開始融化,一隻長尾山雀選擇了緊抓著冰柱不放,而不是在一旁盤旋。結果冰柱墜地,這場「喝冷飲」的表演也就結束了。

圖像來源,Adrian Hirsch
《最後一口氣》,攝影者:阿德里安·赫希(Adrian Hirsch)
在津巴布韋卡裏巴湖(Lake Kariba)的淺灘上,一隻剛出生幾天的新生河馬一直緊靠著它的母親,突然一頭公河馬直朝這兩隻小河馬撲來。它追趕母河馬,然後用自己的大嘴咬住小河馬,顯然是想要殺死它——之後又想淹死和壓死它。心煩意亂的母河馬一直都在一旁看著。阿德里安·希斯基的快速反應捕捉到了這一幕令人震驚的場景。
河馬殺嬰的情況很少見,但可能是因為它們白天休息的水塘乾涸後,過度擁擠造成的壓力所致。公河馬可能通過殺死不屬於自己的幼崽來增加繁殖機會,從而促使母河馬進入發情期,凖備與其交配。公河馬也具有侵略性的領土意識,彼此間殘忍的打鬥並不罕見。如果它們感到有意外遭遇的威脅,也會攻擊和殺死人類。

圖像來源,Thomas P Peschak
《觸摸信任》,攝影者:托馬斯·P·佩沙克(Thomas P Peschak)
一隻好奇的灰鯨寶寶正在接近一雙從觀光船上伸下來的手。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Baja California)海岸的聖伊格納西奧潟湖(San Ignacio Lagoon),灰鯨寶寶和它們的母親們積極地尋求與人類接觸,比如撓撓頭或搓搓背。這個潟湖是組成灰鯨苗圃和保護區的三個地區之一——對於從北太平洋東部倖存下來的灰鯨來說,這是一個關鍵的冬季繁殖地。
捕鯨活動使西部種群瀕臨滅絶,並使北大西洋的種群滅絶。但在20世紀70年代,一條年輕的鯨魚遊近了一位敢於伸手觸摸它的漁夫,鯨魚和人類之間的信任建立起來了。今天許多雌性鯨魚鼓勵它們的幼崽與人類交往。漁民們還在冬季獲得了一筆觀鯨收入——如今,由於魚類數量和捕撈量的下降,這一收入至關重要。在世界遺產聖伊格納西奧潟湖,社區對賞鯨活動進行了精心管理。對資深海洋攝影師和生物學家湯姆·P·佩沙克來說,第一次看到需要愛撫、靠得太近以至於無法聚焦的鯨魚。在這個保護區裏,發號施令的是野生動物。

圖像來源,Jason Bantle
《幸運之洞》,攝影者:傑森·班特爾(Jason Bantle)
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一個廢棄的農場裏,一隻適應性極強的浣熊從一輛20世紀70年代的福特平托(Ford Pinto)汽車中探出頭來,露出一張戴著面具的臉。在後座上,她的五個幼崽興奮地抖動著。這是在附近一處藏身處默默等待的傑森·班特爾也有同感。幾年來,他每年夏天都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
進入車內的唯一通道是擋風玻璃上裂開的小洞,這個洞口的邊緣是鈍邊的,但對郊狼(該地區浣熊的主要天敵)來說太小了,所以這裏成為了浣熊媽媽養家的理想之地。這天晚上,她在出口處停了下來,查看周圍的環境,時間剛好夠班特爾在暮色中長時間曝光。然後她會擠出來尋找夜晚的食物——從水果、堅果、蛋到無脊椎動物和小型脊椎動物。

圖像來源,Eduardo Del Álamo
《如果企鵝可以飛》,攝影者:愛德華多·德拉莫(Eduardo Del Álamo)
巴布亞企鵝是所有企鵝中水下游泳速度最快的一種。當一隻豹紋海豹衝出水面時,它就開始逃命了。愛德華多·德拉莫發現這只企鵝停在一塊碎冰上,但他也看到在南極半島(Antarctic Peninsula)海岸附近巡邏的豹紋海豹,那裏離庫佛維爾島(Cuverville Island)的巴布亞企鵝聚居地很近。當德拉莫的充氣船駛向企鵝時,海豹正好從船的正下方經過。過了一會兒,海報就從水裏衝了出來,張開血盆大口。企鵝趕緊逃離了冰面,這變成了一場捕獵遊戲。
豹紋海豹是一種可怕的肉食動物。雌性長3.5米(11.5英尺),體重超過500公斤(1100磅),雄性略輕。它們細長的身體是為速度而生,寬顎上長著長長的犬齒和尖銳的臼齒,它們幾乎捕食任何東西,從魚類到其他海豹的幼崽。它們也玩弄自己的獵物,比如在這張相片中,豹紋海豹追逐了企鵝超過15分鐘,最後才抓住和吃掉了它。

圖像來源,Ralf Schneider
《像威德爾海豹一樣沉睡》,攝影者:拉爾夫·施奈德(Ralf Schneider)
威德爾海豹(Weddell seal)緊抱著腳蹼,閉上了眼睛,似乎進入了深度睡眠。它躺在南喬治亞州(South Georgia)拉森港(Larsen Harbour)附近的堅冰上,相對安全,不會受到虎鯨和豹紋海豹等捕食者的傷害,因此可以完全放鬆下來。
威德爾海豹是位於世界最南端的哺乳動物,棲息在南極大陸的近海棲息地。它們巨大的身體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脂肪層,使它們在冰冷的海水中保持溫暖。威德爾海豹主要以大型魚類為食,它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潛水員,能夠下潛到500米(1640英尺)以下。這有助於它們在水下長時間捕獵,有時捕獵時間甚至超過一小時。拉爾夫·施奈德從一艘充氣艇上拍攝,緊緊地框住了沉睡的海豹。利用白色背景的冰和陰雲密布的天空的柔和光線,以模仿了工作室的肖像效果,他又將相片調成黑白色,突出了海豹濃密斑駁的皮毛、色調和紋理。

圖像來源,Carlos Pérez Naval
《林間嬉戲》,攝影者:卡洛斯·佩雷斯·納瓦爾(Carlos Pérez Naval)
當卡洛斯·佩雷斯·納瓦爾一家計劃去巴拿馬的索伯利亞國家公園(Soberanía National Park)旅行時,樹懶是他們必去的景點之一。他們沒有失望。幾天來,在公園天篷塔的觀景台上,納瓦爾不僅能拍攝鳥類,還能拍攝這只棕色的三趾樹懶——橙色的皮毛和背上的深色條紋表示它是一個成年的雄性,它掛在一棵天竺葵樹上休息,但偶爾也會沿著樹枝慢慢地移動。
今天早上,森林籠罩在濃霧中,樹懶在移動,納瓦爾決定用一種新的構圖。他走下來,從一個較低的位置向上拍攝,但拍攝角度仍能顯示出樹懶的主要特徵——它的三個鉤狀爪子夾在樹枝上、特有的面具般的眼紋和它又長又粗糙的皮毛。但通過故意把它放在畫面的一個角落,他也捕捉到了森林的氛圍——「環境中的樹懶」。
從2019年10月18日起,年度野生動物攝影師(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的獲獎者將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