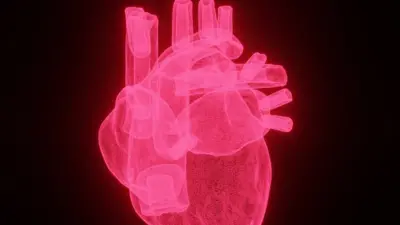在納粹毒氣室當囚工的猶太人是幫兇還是受害者?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 Author, 斯瓦米納森·納塔拉揚(Swaminathan Natarajan)
- Role, BBC國際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為系統屠殺猶太人建的集中營裏有一群特殊的囚犯,自己是猶太人,被組成囚犯特遣隊,負責把其他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然後把屍體從毒氣室拉出來,再塞進焚屍爐火化。
75年前,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解放時,有大約100名猶太特遣隊囚工倖存。
後人對那段歷史的了解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他們的口述。他們是戰時納粹殺人機器運作的目擊者,也是被迫參與者。
達裏奧·葛柏(Dario Gabbai)今年98歲。他曾經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猶太囚犯特遣隊囚工,具體負責把毒氣室的屍體拉出來,塞進焚屍爐火化。
集中營和毒氣室是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絶大屠殺的「終極解決方案」。這個屠殺計劃的終極目的是消滅歐洲所有的猶太人;數據顯示600萬猶太人死於納粹的大屠殺。
葛柏是仍在人世的少數見證人之一。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提醒:本文部分文字和圖片可能令人不適,包括對大屠殺的描述和屍體照片)
「最終解決方案」
1942年,納粹確定了徹底滅絶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計劃,具體做法是自西向東,把德軍佔領區的猶太人全部送到東歐德佔區,或做苦力,或關進集中營,在毒氣室處死,達到種族滅絶目的。
史料顯示,波蘭、匈牙利、希臘和南斯拉夫等國的猶太人大部分死於毒氣室。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和比利時的猶太人有一半遇害,丹麥和保加利亞猶太人則比較幸運,得到當地民眾的保護,大部分得以倖存。
納粹德國文件稱「最終解決方案」處死了510萬歐洲猶太人,但估計實際遇害人數可能高達600萬。
根據這個方案,納粹在集中營挑選部分猶太囚犯組成「特遣隊」,讓他們負責把其他猶太人送往陰間。這些特遣隊成員來自16個國家。
1945年1月27日,蘇聯軍隊解放奧斯威辛。奧斯威辛倖存者留下了大量親歷者、目擊者回憶錄。
但是,倖存的囚犯特遣隊成員卻似乎全部啞口無聲。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特殊使命
1980年代,以色列歷史學者吉迪安·格雷夫(Gideon Greif)教授開始搜集有關集中營囚犯特遣隊的資料,希望揭開這段歷史謎團。
格雷夫教授對BBC解釋自己這麼做的動機:「我的目的之一是幫他們改善形象。我剛開始這項研究時,他們被視為幫兇和劊子手。但他們其實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普裏莫·列維(Primo Levi)在回憶錄《溺死者和獲救者》(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寫道,組織猶太人囚犯特遣隊是納粹罪行中最殘忍的惡行。
格雷夫教授贊同這個觀點。他認為,這種迫使同族自相殘殺是極端殘忍的手段。

圖像來源,Gideon Greif
尋找逝者
格雷夫博士的第一部專著,《我們欲哭無淚》(We Wept Without Tears),記錄了31名前納粹集中營囚犯特遣隊倖存者的經歷。
黨衛軍士兵是劊子手,囚犯特遣隊成員被迫充當助手。
在黨衛軍的監視下,他們必須搜檢毒氣室的屍體,取出受害者藏著的值錢物品和金牙,然後再把屍體塞進焚燒爐。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奧斯威辛集中營沒有什麼照片,但蘇軍解放了集中營後設法重建、重現了囚犯特遣隊的恐怖經歷。
葛柏的分工是剪下女屍的頭髮,收集整理好。
那段經歷和精神折磨幾十年後仍恍如昨日。2018年,他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猶太大屠殺基金會(USC Shoah Foundation)重溫自己當年目睹、親歷的恐怖,和自己承受的心靈折磨。
「我不斷問自己怎麼能承受這一切?上帝在哪裏?」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他在集中營遇到的一位波蘭囚犯告訴他,要堅強。他之後時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堅強。
「我對自己說,我就是個機器人......閉上雙眼,別多問,該幹什麼幹什麼。」
懲罰
葛柏必須服從指令。作為猶太囚犯,他要生存就別無選擇。而且還不能顯露絲毫的懈怠。
動作稍有遲緩或效率不高就會招致殘暴的懲罰。
有時黨衛軍士兵會檢查正在送往焚燒爐途中的屍體。他們要是發現有一顆金牙被漏拔了,造成疏漏的特遣隊成員有可能被直接扔進焚燒爐活活燒死。
其他懲罰方式包括射殺、酷刑、毆打,還有脫光衣服倒在碎石地面上被人推著滾動。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為了殺一儆百,一人受罰,其他特遣隊的人必須在場旁觀。
而且,特遣隊也不是生存的保障,因為納粹每隔半年就「新舊更替」一次,殺了老人,用新人接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幫兇」的處境還不如一般的囚犯;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擔驚受怕,天天目睹千百人被屠殺,自己則被迫搜檢屍體上值錢的東西。
格雷夫博士說,在那種狀況下,活下去不容易,連保持求生的願望都很難,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毒氣室
不過,還是有人活下來了,就像葛柏,而且還打破沉默,公開講述當年在集中營死亡工場的經歷。
後人因此得以了解死亡工場的恐怖內幕和運作細節。
「他們關上門,然後黨衛軍從門上方三、四個開口把齊克隆B(氫化物)扔下去。大概5分鐘之後,屋裏的人就被毒死了。靠近門的那些人最早吸入毒氣,1-2分鐘就死了。」
毒氣室用的齊克隆B是晶狀顆粒,一接觸空氣就變成致命的毒氣。

圖像來源,The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但求速死
格雷夫博士的書裏記錄了葛柏的兄弟雅科夫(Ya'akov Gabbai)的經歷。
雅科夫也被編入毒氣室特遣隊。有一天他看到自己兩個表兄被趕往毒氣室。他偷偷叮囑他們,進屋後盡量靠近門口,挨著門上的通風口。
反正要死,不如速死,可以免遭更多痛苦。
保持尊嚴
格雷夫博士說,許多在毒氣室特遣隊呆過的人心理上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
他說,為了承受這種死亡工場和親身參與其中的巨大心理衝擊,出於人自我保護的本能,特遣隊成員喪失了情感,變得無情無感。
「那並不是說他們變壞了,變惡毒了。他們中有些人告訴我自己曾經如何設法盡可能讓猶太受害者保留一些尊嚴。」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格雷夫博士見到的第一位集中營囚犯特遣隊成員叫約瑟夫·薩卡爾(Josef Sackar)。那是1986年。
薩卡爾記得,他經常被分派到女囚犯被勒令脫衣服的地方。
為了不讓她們太難堪,他總是把頭轉向別處,視線避開她們。
另一位,肖厄爾·查桑(Shaul Chasan)被分派去毒氣室搬屍體,把屍體碼在通往焚屍爐的升降梯上。
他告訴格雷夫博士,自己當年曾特別留心不把屍體在滿是泥土和垃圾的毒氣室地上拖來拖去。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為逝者祈禱
當年那些被迫進特遣隊的囚犯大部分是虔誠的正統猶太教徒,大部分時候每天盡量保持做三次禱告。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還能湊齊10個人一起集體禱告。集中營看守不在的時候,他們還會在焚燒屍體過程中為逝者念禱告詞。
大批遣送匈牙利猶太人期間被挑選出來當特遣隊的人當中,到二戰結束時倖存者不到100人。

圖像來源,The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館的記錄顯示,1944年5月,納粹大批遣送匈牙利猶太人,8周時間內42.4萬猶太人被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自那以後,屠殺明顯升級。
毒氣室效率高,屠殺速度超過了集中營焚屍爐的承受能力。主管焚屍爐的德國軍官不願暫停屠殺,於是下令挖露天焚屍坑。
一張偷拍的露天焚屍坑的照片為日後戰爭法庭和歷史學者提供了珍貴的證據。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反抗
施羅莫·德拉根(Shlomo Dragon)在集中營囚犯特遣隊時曾目睹罕見的英勇反抗行為。
他記得有一位婦女拒絶把衣服全脫光,於是集中營的總管、黨衛軍軍官希林格拔出槍,把槍口對凖她,命令她把內衣脫掉。
她解下胸罩,在他面前揮舞,然後揮拳打他。希林格手裏的槍掉在地上,她一把撿起槍,瞄凖,扣扳機,他當即斃命。
後來,人們普遍認為這名勇敢的女性是波蘭舞蹈演員弗朗切斯卡·曼恩(Franceska Mann)。她死後成為一個傳奇人物。
還有一名特遣隊囚工曾目睹一群波蘭兒童赤身裸體,排著整齊的隊列,齊聲詠唱著禱詞,秩序井然地走進毒氣室。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無奈
特遣隊囚犯的食物配。給和生活條件比其他囚犯略好,還有機會穿受害者身上脫下的衣服。
格雷夫博士說,跟他們受的磨難相比,這些根本不值一提。囚工們住在不同的囚室,始終被德國衛兵監視。
他們也曾反抗,結局慘烈。
1944年10月7日。策劃反抗的是兄弟倆。格雷夫博士說,那次事件堪稱猶太人的壯舉,應該用金粉銘刻。
當時數名特遣隊囚犯用石塊襲擊黨衛軍士兵,還縱火焚燒一個焚屍爐。事件很快被平息,451名特遣隊囚工被處死。
罪行的記錄
有些特遣隊囚工當時曾在紙上寫下自己的經歷和心情。

圖像來源,IFZ-MUENCHEN.DE
馬賽爾·納加裏(Marcel Nadjari)是希臘猶太人。
他1944年11月寫下這句話:「我悲哀的不是自己死到臨頭,而是因為無法用我渴望的方式復仇。」
他還記錄了一些數據,包括一名成年受害者的骨灰重量大約是640克。
他的獄中日記共13頁,全部捲起來藏在一個保溫杯裏,蓋子上套一個塑料袋密封,然後把這個保溫杯裝進一個皮口袋埋到地下。
多年後,他和其他一些囚工的日記被發現,經過整理、修復、翻譯,最後編撰成集,《奧斯威辛書卷》(Scrolls of Auschwitz)。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正義
戰後,一些集中營特遣隊囚工曾作為證人在戰爭罪法庭指證當年集中營的看守和衛兵。
美軍軍事法庭審判奧斯威辛集中營黨衛軍軍官奧托·莫爾(Otto Moll)時,亨裏克·托伯(Henryk Tauber)在證人席上指證他多次把活人扔進焚屍爐活活燒死。
莫爾最終因為在猶太種族滅絶大屠殺中擔當的角色被判絞刑。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當意識到敗局無法避免時,德軍從1945年1月中旬開始撤離集中營。
將近6萬名饑寒交迫衣不遮體的囚犯被迫在零下20度的嚴寒和積雪中步行向50公里開外的市鎮轉移。
行進中跟不上的人就地開槍打死。
罪不容赦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屠殺現場,估計有110 萬 - 130萬人在那裏被殺害,其中90%是猶太人。
這個受害者數目超過了英國和美國在二戰中死亡人數的總和。
然而,許多納粹戰犯逃脫了法律制裁。
BBC/PBS聯合攝製的系列紀錄片《奧斯威辛》中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總共有大約7千名納粹軍人,受到法律懲處的只有大約800人。
格雷夫博士說,不能讓任何一名納粹戰犯逃脫懲罰。

圖像來源,Gideon Greif
他經常到歐洲的納粹戰犯審判庭上提供專家證詞。
他說,納粹曾設法銷毀罪證,導致文件檔案空白,而這個空白只能由倖存者的回憶來填充。
於此同時,他也設法為改變了公眾對被迫在毒氣室當囚工的猶太特遣隊的看法。
他說,現在沒有人會把這些囚工稱作納粹幫兇了。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葛柏是現在唯一還在人世的納粹集中營特遣隊囚工,也是幾十年來納粹戰犯審理法庭上一名孤獨的證人。
他住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身體虛弱,疾病纏身,幾乎沒有力氣開口說話。
不過,5年前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70週年時,他曾重返舊地,參加紀念活動。
他當時接受BBC採訪時這麼說:「我告訴自己,戰爭總有一天會結束,我要活到那一天,把這些事告訴全世界。」
.